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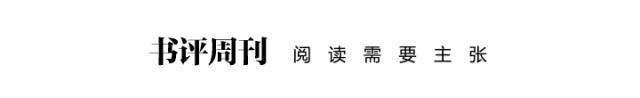
如果诗歌在哪一个时代是被轻视的存在,这并非诗歌的不幸,而是时代的不幸。时代往往不知道如何对待诗歌,于是诗歌也学会了时代的态度,那就是蔑视时代。通常,最先屈服的又是时代,而诗歌却始终骄傲。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诗歌应该是历史的姐妹,在荷马看来,恐怕诗神还应该是九位缪斯女神之首;而时代,如果运气好的话,应该是历史的有教养的女儿。那么,历史为什么就不能将时代托付给诗歌养育呢?莎士比亚深谙这一点,于是经常让诗剧中的人物吐槽时代,哈姆雷特有一个基本判断是,时代脱节了,而他似乎只有依赖诗歌的智慧去纠正时代。

作者 | 王东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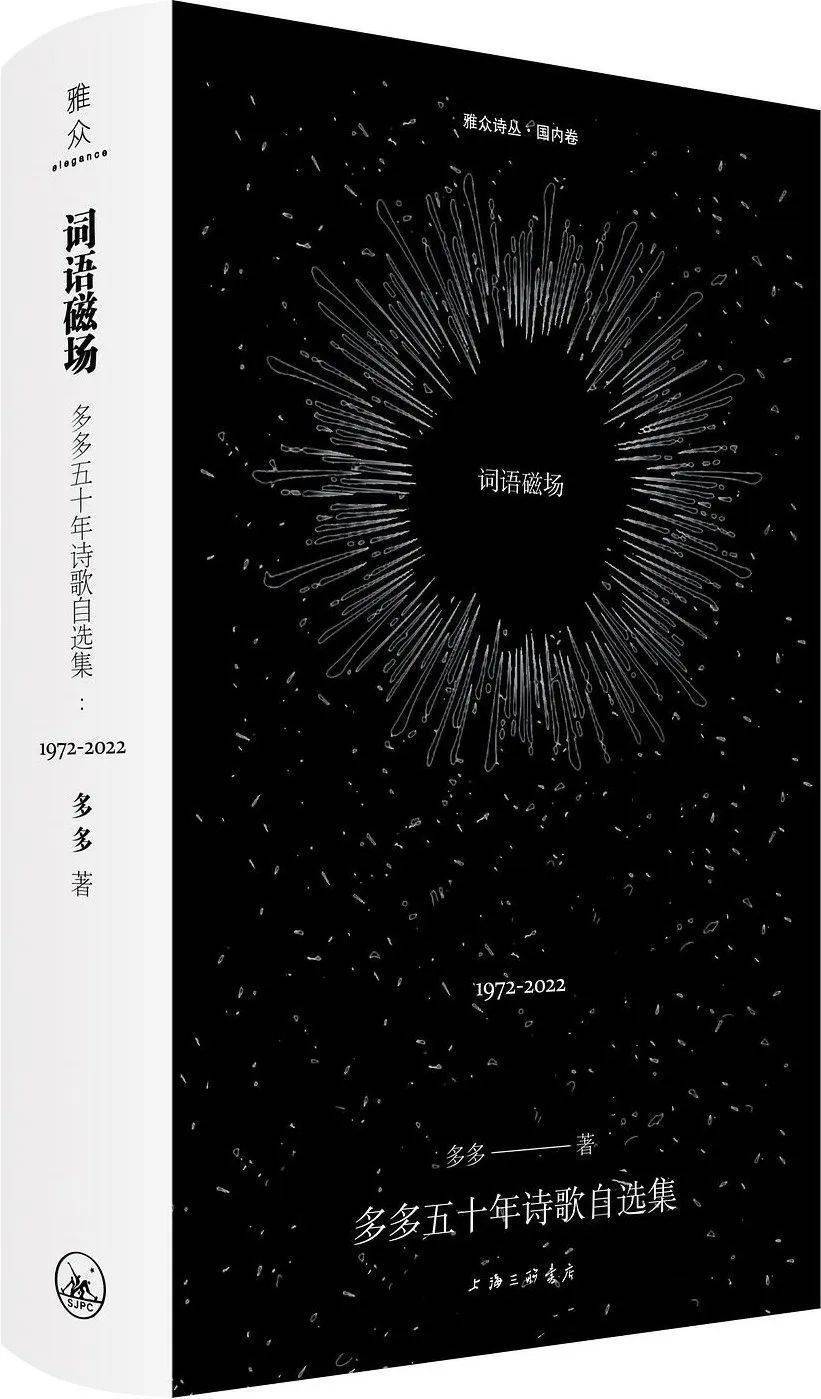
《词语磁场:多多五十年诗歌自选集 1972-2022》
作者:多多
版本:雅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
2025年3月
忠诚于语言的诗人
多多将他最近出版的两本诗集分别命名为“拆词”和“词语磁场”,体现出一种语言的诚实:诗人忠实于语言,与语言为伴,并以语言为生。然而,这里毫无神秘可言,亦非故弄玄虚。语言之于诗人,一如颜料之于画家,是可以注视和触摸的;一如音符之于音乐家,是可以听闻和称量的。多多在《制作一幅画》(2017年)中写道:“一如醒来后又再次入睡/一幅画已在这里//创造,是无中生有的行动”。诗人沉浸于语言的创造,并以此见证着世界的创造,二者几乎融合为同一个过程。
多多,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当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1980年代末出国,旅居英国、荷兰等地,2010年被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做驻校诗人。著有诗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行礼:诗38首》《多多诗选》《多多四十年诗选》等。
在《抒情诗的教化,与词的命运》中,我曾谈到多多对诗歌创造力的理解,近似于一种元诗观念。其根源其实在于宗教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诗学,并由于20世纪的语言本体论而得以放大甚至漫漶无边。
元诗观念在当代广为人知,主要是由于张枣的倡导,其实这一观念在不同诗人那里都有表现。记得当年与张枣聊天,他主动说多多是一位大诗人。我谈到这一点是想表明,诗人们对语言奥秘的领悟虽然有所不同,彼此又都可以心领神会。通向语言的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条。张枣曾经认为“朦胧诗”一代的写作也发生过“元诗转向”,这一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补充的是,多多可能是这个群体中最早触及语言本体的能量并一直坚持到现在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是一位忠诚于语言的诗人,甚至可以说是语言本体论的激情在当代诗歌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也不需要像张枣那样提出元诗观念,而只需实践就可以了,后来的诗人却要面临语言本体论的压力,并试图提出种种折冲樽俎的理论命题。
按说,语言本体论(linguistic turn)的转向,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上是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但在多多的诗歌中发生得更早,甚至开始于七八十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语言思想与语言哲学其实并非新鲜事,在诗人写作的那一刻,语言哲学就开始了。20世纪的哲学家面对诗人时比较谦虚,开创了一个阿甘本所说的哲学上的“诗人时代”。
《拆词》
作者:多多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10月
诗的智慧包含历史思考
诗歌的智慧包含语言,但又不能减缩为语言。现代主义诗歌批评更为注重对语言、形式的实证主义的、现象学的分析,并成为当代诗歌批评的主流。这和古典批评似乎是相反的。19世纪文学批评中的道德意识,在20世纪则分裂为政治意识和语言意识,二者相互攻讦,有时又相互为用。我要说的是,诗歌的智慧不能只是简化为语言或手艺问题,就像不能被简化为政治问题一样。
不过,即使在当代中文系的课堂,新诗也显得像是一门外语,“除了我的窗户,朝向我不再懂得的语言”(多多《没有》1991年)。中文系师生都明白,小说中可谈论的比诗歌中要多,就是因为诗歌似乎只剩下了语言。另一方面,多多写下了多少值得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进行细读的诗?我以为,其数量是远远超过其他诗人的。在这方面,诗人的语言创造与反资产的语言资产,并未被诗歌批评与理论充分消化。这方面的话就此打住。
在多多诗歌中存在着一种令人心折的紧张,除了源于个人的性情禀赋,这种紧张更多来自于历史和时代本身。诗歌的智慧中也包含了一种历史思考。一般来说,一个年轻诗人开始写诗时,可能会有一种反历史、非历史的冲动,甚至想要从历史中逃离出来,但随着年岁增长,他就会再次震惊并痴迷于历史之谜。在1970年代初,多多就找到了自己的写作主题,历史力量与自然力量的较量,这也是古典汉语诗歌的基本主题。然而,多多这时的责任更多是将自然从历史中剥离出来。1973年的《海》这样写道:
海,向傍晚退去
带走了历史,也带走了哀怨
海,沉默着
不愿再宽恕人们,也不愿
再听到人们的赞美……
这样纯粹的抒情诗包孕良多。多多需要从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和斗争哲学中逃逸而出,才能感受到自然的亲切力量:“绿色的田野像刚刚松弛下来的思想”(《告别》1972),这一代人将自己绑上了“自由的十字架”,“在自由的十字架上射死父亲”(《致情敌》1973),多多的紧张可能最终来自于辩证法。在1980年代的诗歌中,自然的力量甚至可以推动历史,“季节,季节/用永不消逝的纪律/把我们种到历史要去的路上——”(《北方的土地》1988),自然的力量逐渐占了上风,然而,犹有对斗争哲学的善意理解:“斗争,就是交换生命”(《十月的天空》1986)。而在1990年代,由于孤悬海外,多多诗歌中更多了一种抽象的文明之思。
多多画作,图片出自诗集《拆词》,出版社供图。
在希腊神话的九位缪斯女神中,诗神与历史缪斯是姐妹关系。这并不令人意外,有趣的是后世或有的如下争论:二者孰长孰幼,抑或谁更聪慧?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真理比历史的真理更高,另一个翻译更为直接,诗比历史更有智慧。中国一向有诗史传统,强调诗史互证,近世陈寅恪提出“以诗证史”,其实是将诗歌想象力当作历史研究的补充。中国的历史观念在起源上可以追溯到巫觋,也就与诗歌脱离不了干系。
一如其他文学体裁,诗歌可以呈现丰富的历史感性和历史细节。从历史的角度阅读诗歌,构成了一种充分释放诗歌能量、增加诗歌“价值”的读法,可以让我们看到,诗歌的智慧并不简单。
在理论上可以说,即使是高度纯粹的抒情诗,也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与历史建立起关系,从中不仅可以窥见个人的生存体验——与作者的隐私无关——更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历史感性。如果我们意识到多多的诗歌充满了预言性——他可能更像是当代诗中的大巫师——就不得不承认从历史的角度阅读多多诗歌极具难度和挑战性。
他同时还是一个末日论者,这可能加强了他诗歌中的紧张感,在这个意义上,多多诗歌中的历史经验和生存经验是经过高度浓缩和挤压的,但这就是他承担历史和时间重力的方式。面对时间,诗人有一种天生的紧迫感,但也会因诗歌而得救。如果诗人放松下来,我们会怀疑如此紧张的诗行是否还会被写下,但也有可能在诗歌中出现祈祷、得救的平静时刻。
多多诗歌的哲学式阅读
除了语言的阅读和历史的阅读,多多的诗歌还可以接受一种终极的阅读,那就是哲学的阅读。
并不是所有诗歌都值得这一种阅读方式。我一直引以为憾的是,中国当代的思想者和哲学从业者未能将当代汉语诗歌纳入视野,而西方顶尖的思想家很多都是谈论诗歌的高手,不管是将诗歌作为思想的材料,还是受到诗歌启发,以哲学思想为诗歌作注释。其实,多多对“思”的触及有一个生活和艺术过程,并不抽象晦涩,恐怕也只有如此才显得可信:“从蒙面女人眼神中射出的恨/亦集中了她全身的美,既/弯曲了思,又屈从于思……”(《在突尼斯》2000),“蒙面女人”代表着一种被压抑的性别和经验。从一开始,多多似乎就对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有一种悲观的理解:“思想,是那弱的/思想者,是那更弱的”(《墓碑》1986),换言之,是行动塑造了历史。
梵高画作。
哲学的读法与语言的、历史的读法并不冲突。在诗歌的哲学读法中,可以包含语言思想或语言哲学,多多这一类诗歌值得注意的有《无语词语》《向内识字》《词语风景,不为观看》《词如谷粒,睡在福音里》《词语磁场》《在无词地带喝血》等。也应该包含存在哲学,《只有几本书》(2014)中有这样的句子:“让是成为是”。还应该包含历史哲学:“多好,古墓就这么对着坡上的风光/多好,恶和它的饥饿还很年轻”(《痴呆山上》2007),只有如此诗歌才可以感应未来,“大量的未来/再次奔向文盲的恐惧”(《年龄中的又一程》2007)。
多多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越来越枯瘦,也是由于接近于思或哲学的缘故,虽然在个人的思想品味上,多多更喜欢谈论神秘主义或神秘学。他甚至偶尔放弃了自己歌唱性的长处,某些诗,如《两者》谈论爱与虚无,索性就是哲理诗。对多多诗歌的哲学阅读还应该触及中西思想比较与融通的关键,也即超越性或宗教问题:“这无神时刻的无助//一个只有墓地的世界多么凄凉”(《收获时节》2010),“所有的时代排列起来/像主的记忆一样遥远”(《在胡杨林醒着又死着的岁月》2009),“一朵被解构的玫瑰/流放了人对神的注释”(《词语从哪里来》2022)。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王东东;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
睿迎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